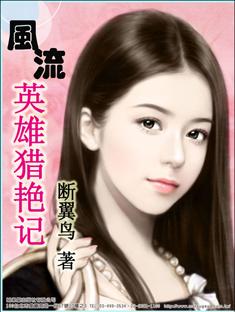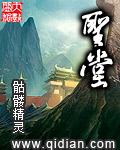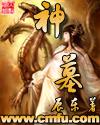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第11部分(第2页)
1954年为适应新形势,由中央民委副主任、民族出版社社长萨空了倡议,中央民委向出版总署报批,总署于1954年4月正式同意由民族出版社从1955年1月起创办《民族画报》。同时,《人民画报》“副册”自1955年1月停刊。由周恩来总理题写刊名,我国第一本以反映少数民族生活为宗旨的大型画报《民族画报》按时问世。办刊经费由政府拨专款予以补贴。
“《民族画报》创刊初期的全体工作人员”合影照片中,站在后排、身材修长的庄学本面带微笑,鼻梁上架着眼镜,俨然一个大家庭中敦厚、淡定的长子,再也没有当年的漂泊容颜。革命大家庭给他带来了安定。
《民族画报》历届领导班子名录这样记述:
1955年2月—1958年3月编辑部副主任庄学本
1958年4月—1964年编辑部副主任郝纯一、庄学本
1964—1979年6月编辑部副主任郝纯一、林扬、庄学本
有关单位体制内庄学本工作生活状况,相关媒体仅有这样简略的记述:
《民族画报》创刊后,庄学本作为编辑部副主任,负责主持画集的编辑出版,间或外出采访。其间,他还完成了“养獐取麝”的科学研究工作,后获卫生部颁奖。
一位被后来的“发现者”称之为“摄影大师”的庄学本,以“养獐取麝”——这项科学研究工作获奖,作为自己人生的成就,被记录下来。
1957年,庄学本是如何认识自己影像价值的呢?他的那些陈年旧影与主流价值取向到底有无差距呢?那一年,中国摄影学会为他举办了个人影展,他在《写在个人影展之前——用摄影机反映少数民族的生活》一文中以谦逊的语调,道出了自己的困境:
中国摄影学会要我举办一次个人影展,当时未经深思就接受了。
但在选择照片时不免又感到为难,因为学会要求展出的图片应该是在摄影艺术上比较成功的作品,而我过去在摄影时往往是随手拈来的一些记录性的照片,对艺术上很少下过工夫。所以在展出图片的选择上,不得不降低了艺术标准而多照顾一些民族特点,但在民族一面要求,又显得材料零零星星,遗漏了许多重要的内容。
虽然“受到重视”,得以在中国摄影学会主持下举办20世纪50年代难得一见的“个人影展”,但此刻,办公室内身着规规矩矩中山装的庄学本还是敏感地体悟到,自己年轻时代拍下的那些老照片,与新政权下的影像诉求已经有了不少距离。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以俄为师的神话
1957年,十月革命纪念日到来前夕,新华社摄影部袁苓撰文《向苏联摄影记者学习》,回忆起自己1955年作为“自己人”在塔斯社摄影部学习、工作的经历。②
这篇回忆文章出自“反右”高潮阶段,“我国人民以万分欢欣鼓舞的心情庆祝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之际,自然会有不少应时之语。新闻界人士在向苏联学习方面,也经历了从1949年到1955年间一个时期内对苏联经验全盘接收,到1956年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所引发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震荡,及以1956年7月以后《人民日报》为首的新闻工作改革期间,新闻界在某些方面对苏联经验的质疑,甚至全盘否定学习苏联新闻工作经验的历史必然性与受益方面,出现了短暂的“回归”——主张学习1949前中国资产阶级报纸的传统。①
此时,借纪念十月革命之机,重新提出“在新闻战线上,在中苏兄弟间”,再次肯定新闻界向苏联学习的经验,自然面对的是比之前些年更为复杂的语境与心态。在新闻摄影界,面对苏联这一“他者”,从技术、操作层面上的全盘模仿,到意识形态方面因时局变化而出现的反复,几年来,也颇多变局。纵然如此,袁苓还是对苏联新闻摄影做了“一边倒”的热情礼赞与全盘肯定。而袁苓的个人经历与这篇文章本身都可看作承载这一问题的“标本”之一种。
除了个人在塔斯社学习期间所感受到的“赤诚友谊”外,袁苓还再一次温习了塔斯社走“社会主义道路”方面的有益经验。
在我们访问塔斯社摄影部的时候,摄影部的领导人明确地指出,新闻摄影是党的新闻事业的一部分,列宁办报的原则(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者和集体的鼓动者,而且还是集体的组织者),是国家通讯社的原则,其中包括摄影部。他们说:“我们从生活中寻找这样的事实,来动员人民完成党和政府的决议和他们的任务。我们发出的照片都要有明确的目的,就是说它要明确地向读者表现什么,号召读者做什么,对读者有什么教育意义,告诉读者新的东西。”
袁苓认为,我们与塔斯社在强调新闻报道必须服从*的要求,要对人民群众有指导性,这样的“根本原则”问题上是一致的。而“右派”分子说我们强调从政治要求出发,就是不顾摄影的特点的“主观主义”;并说用党的新闻事业的根本原则来要求新闻摄影是“教条主义”。很显然,他们是从根本上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
在此问题上,袁苓理解的“塔斯社经验告诉我们”:摄影记者不仅要正确挑选事实,而且在选择场面和时机的时候,在开镜头之前,也要正确判断所选择的每一具体场面或情节是不是最精彩的,会给读者什么影响。
照片的形式和内容的一致,也是塔斯社新闻摄影工作的一个原则。摄影部的领导经常提醒记者,作为摄影机构,所作的报道是摄影报道,所以稿件的形式应该看作重要的问题。一张好照片应该主题是好的,摄影技术是好的,而且构图是成功的。但同时他们也反对摄影记者在形式上玩弄技巧、哗众取宠。在此,袁苓看到了政治原则之外的、新闻摄影“专业性”的一面,并反思了自己过去在这方面存在的“两种相反的毛病”。
袁苓所指的“两种相反的毛病”,也正是20世纪50年代中国大陆新闻摄影界在“内容与形式”问题上纠缠不清的两难论题。按照他的现身说法,一是拍摄过程简单化,潦潦草草,有单纯记录的气息。这种照片被批评者诟病为“自然主义”。另一种状况是,片面追求形式上的美,使形式离开了内容。这又被指责为犯了“形式主义”的毛病。但,二者的度如何把握,边界在哪里呢?
袁苓认为自己在这些兄弟、师长面前找到了答案:“正确的方法是把两者统一起来,在根据整个报道的要求选择场面和情节时,既是内容的选择又是形式的选择。”
为了保险起见,在拍摄照片以前还要反问自己一下:在照相机里的未来的照片将是怎样,能不能吸引读者,能不能使读者通过形象的感受而产生更深刻的印象,使读者通过形式看到更深刻的思想。如果相信能够这样,那么就大胆拍摄;否则就要检查一下,一定有偏差。
置身于“这些记者像兄弟似的给我以关怀,像兄长似的给我以教导”的环境中,袁苓不但顺利完成了实习计划,而且看到了“摄影记者的生动的榜样”。这让他折服;或者说,他被自己的描述折服了。
概括地说来,塔斯社摄影记者们是这样的:自觉的、热情的党的宣传员,严肃、活泼、干练的新闻记者,技术熟练、有艺术修养而富有经验的摄影家。
不过袁苓又退了一步,虽然并不是每个摄影记者都达到了这样的水平,但年轻记者们都在自觉地按照这个要求工作着。在他看来,塔斯社的摄影记者们都极其关心政治,有着很高的工作效率,技术素养高,并且还有“一个共
张三丰弟子现代生活录
张湖畔,张三丰最出色的弟子,百年进入元婴期境界的修真奇才。他是张三丰飞升后张三丰所有仙器,灵药,甚至玄武大帝修炼仙境的唯一继承者,也是武当派最高者。在张三丰飞升后,奉师命下山修行。大学生,酒吧服务员,普通工人不同的身份,不同的生活,总是有丰富多彩的人生,不同的遭遇,动人的感情,总是让人沉醉不已。武林高手...
风流英雄猎艳记
生长于孤儿院的少年刘翰和几女探险时偶得怪果奇蛇致使身体发生异变与众女合体并习得绝世武功和高超的医术为救人与本地黑帮发生冲突得贵人相助将其剿灭因而得罪日本黑道。参加中学生风采大赛获得保送大学机会。上大学时接受军方秘训后又有日本黑龙会追杀其消灭全部杀手后又参加了央视的星光大道和青歌大赛并取得非凡成绩。即赴台探亲帮助马当选总统世界巡演时与东突遭遇和达赖辩论发现超市支持藏独向世界揭露日本称霸全球的野心为此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而在颁奖仪式上其却拒绝领奖主人公奇遇不断出现艳遇连绵不...
师娘,借个火(师娘,别玩火)
师父死了,留下美艳师娘,一堆的人打主意,李福根要怎么才能保住师娘呢?...
圣堂
一个小千世界狂热迷恋修行的少年获得大千世界半神的神格,人生从这一刻改变,跳出法则之外,逆天顺天,尽在掌握!骷髅精灵不能说的秘密,尽在火热圣堂,等你来战!...
魔师逆天
前世孤苦一生,今世重生成兽,为何上天总是这样的捉弄!为何上天总是那样的不公!他不服,不服那命运的不公。自创妖修之法,将魔狮一族发展成为能够抗衡巨龙的麒麟一族,成就一代麒麟圣祖的威名。...
神墓
神魔陵园位于天元大6中部地带,整片陵园除了安葬着人类历代的最强者异类中的顶级修炼者外,其余每一座坟墓都埋葬着一位远古的神或魔,这是一片属于神魔的安息之地。一个平凡的青年死去万载岁月之后,从远古神墓中复活而出,望着那如林的神魔墓碑,他心中充满了震撼。沧海桑田,万载岁月悠悠而过,整个世界彻底改变了,原本有一海峡之隔的...